大伯,大伯散文
听说大伯患了脑瘤,我一时间又惊又痛,难以置信。无奈现代医学仪器太先进,彻底粉碎了亲人们但愿是误诊的幻想。省城的医生说了,为大伯做手术的意义不大,好好的一个人走着来,是要抬着回去的,何苦要老人遭这个罪,还是回去好好在老人跟前尽点孝道吧!
看望大伯,是强装着笑脸去的。做人本分厚道,勤劳持家一生的他,人生的晚境却要遭受病魔的摧残,想想实在令人心酸。大伯看见我进门,唤着我的小名,招呼我快坐,忙唤大妈给我倒水,自己拧开炕头的风扇让我凉快凉快。我强忍哽在喉头的酸涩,坐下来和大伯说话,嗔怪他不顾惜身体,村东村西四处揽活干,累垮了自己没人能替。大伯笑着听我数落他,说是年岁不饶人,承认自己替儿女操的心太多,最近经常感觉头晕,吃饭没胃口,啥都干不动了。听医生说,他没啥大病,血压低,歇些日子就好了,还怪大哥他们带他去城里检查乱花钱。我怕再说病情会黯然伤心,忙岔开话题,和大伯聊起了家常,聊起他小时候的生活状况。好多年没时间听大伯讲那些陈年旧事,今天见大伯打开了话匣子,就饶有兴头地问东问西。听大伯讲那些过往的岁月,对大伯又多了些敬意,心里越发难过起来。勉强陪大伯吃了中饭,让它歇着安心养病。回到母亲家,刚看见两鬓斑白酷似大伯的父亲我眼泪就突然流出来,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。
第二次去看大伯是在一个月之后。听母亲说大伯瘦得厉害,吃得极少,精神大不如先前了。偶尔在外面闲坐,呆呆地闷着头不言语。亲戚们都陆续赶来看望他,让大伯意识到自己的'病大有来头。他再也不吵着要去医院买开胃的药了,小妹劝慰他别多想,他说:我都这把年纪了,还瞒哄啥呢?谁能强过命嘛。好吃好喝的堆在眼前,大伯却没了胃口。听大妈说,大伯晚上睡不着,也不说话,一个人摸索着起来,拉开门信步出去漫游。可怜大妈不敢惊扰大伯,只能悄悄跟在他后面走。大伯一会驻足望望天,一会停步望望寂静的村庄,一会边走边叹气。绕着村子走一遭,再回来睡下,一声都不言语。大妈只能悄悄抹眼泪,她知道那是大伯抛不下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。又过了个把月,我再去瞧大伯,他已经认不出我是谁了。朝夕相伴的亲人,几十年的同胞兄弟一概认不清了。看见有人来瞧他,他脸上会露出恍惚凄凉的微笑,想说什么,已无从说起,因为记忆衰竭,他视睡如归,偶尔言语一声,也是含混不清。眼看着大伯一天天衰弱下去,我心中悲苦,却无可奈何。
大伯走了,永远地撒手而去。只能在梦中或另一个世界相见了。盛殓之前,大妈一遍遍地走到灵床前,揭开大伯的蒙脸纸,摸索着大伯的面孔,抻抻他的衣服,叮咛他闭上眼放心走。忽然,大妈坐在炕沿放声大哭,悲悲切切哭诉着:冤家呀,你把我一脚蹬在半道上,让我咋活呀!冤家呀,你辛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,说撒手就撒手呀……大妈揪心扯肺地哭声,像利刃一般刺痛了每个亲人的神经,一时间都想起了大伯的好,都禁不住大放悲声。
万物皆有生死,唯有记忆不灭。最早的记忆来自大伯对我的疼爱。依稀记得五六岁的光景,姐姐带着我在路边的地里拔猪草,我看见大伯骑着自行车赶集回来,就乐颠颠地跑向大伯,锐声喊着要坐大伯的车回家。大伯叮嘱姐姐拔完草早点回来,就抱起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。在姐姐的羡慕嫉妒中,我得意激动地拽着大伯的衣襟,任凭大伯载着我在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上,颠簸飞翔。可是我的脚却突然塞进了车轱辘内,当大伯把我的脚从车辐条内掏出来时,脚踝骨已蹭掉了皮,血红一片,我害怕地大哭。大伯一边责怪自己太粗心,一边安抚我,说带我去他们家,让大妈给我炒鸡蛋吃,免得我妈看见了责怪。每次当我和姐姐因淘气或做错了事被脾气火爆的母亲撵出家门时,大伯家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。围坐在大妈的热炕头上,吃着大妈炒的豆子,听大伯边剥玉米边为我们讲那些稀奇古怪的鬼狐故事,我和姐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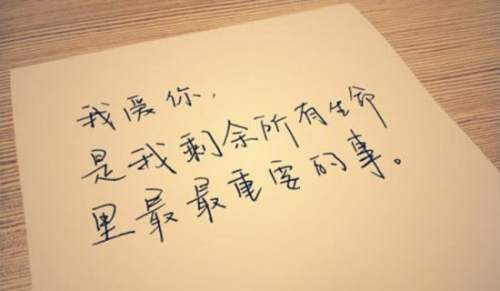
大伯年轻时学了一套做豆腐的手艺。逢年过节或赶上村里过红白喜事,大伯和大妈就忙得整宿不睡觉。泡豆、磨浆、过滤、烧火、点卤、压包,大人孩子各有分工。拂晓时分,大伯就挑起豆腐担子,送货上门或走街串巷地吆喝他的生意。时常见大伯停在某个场院中为乡亲们称豆腐的情形。他一边询问主人家怎样待客,一边麻利地为主顾割豆腐过称,过完称总不忘再割一块给添上点,碰见相熟的女人,就会开玩笑说:孩子他干爹来了没?称二斤豆腐给他吃吧。此等打趣的疯话,自然会招来女人的笑骂,主顾乡邻都会笑成一片。为了能吃上大伯拌了辣子蒜泥香醋的豆腐脑,我经常帮大妈捡豆子、拉风箱、烧火,跑腿替大伯去小卖部买烟。大伯就是靠着做豆腐、作务果园,驮筐做小生意和四处打工,一点点积攒下家业,帮三个儿子娶了亲,盖了房,立了门户。
作为长子长兄,大伯从小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。爷爷老实憨厚,幼年失怙,娶亲之后另立了门户,在生产队的马房里安了家,没有任何根基和庇护,靠爷爷奶奶给大户人家当雇佣来勉强度日。大伯十岁时就能给生产队放羊,就能帮大人分担家务。记得大伯说他十五岁时正赶上闹饥荒,能吃的野菜树叶都被吃光了,兄弟们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再不想办法弄吃的,只有饿死的份。情急之下,大伯毅然去外村家境殷实的表姑家借粮。大伯向表姑诉说了家里揭不开锅的恓惶,乞求表姑怜念他们哥几个可怜。善良的表姑背着家人,装了一袋子玉米,让大伯走后门回家。背了粮食口袋,边走边抹泪的大伯刚一回家,就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爷爷病逝后,大伯就成了除奶奶之外的二当家。他让三叔学打铁,送四叔去当兵,送五叔读高中,带着父亲一起去山里扛木料,挖药材,一起驮着筐子贩水果卖蔬菜,风里雨里哥俩总是在一起。哥几个成人后,大伯和奶奶相继帮他们娶了亲,建了房,那其中的周折、艰辛、难肠、酸苦,自是不言而喻。在我记忆中,哥几个先后都住上了土木结构的瓦房,唯有大伯还住在老宅的三间草棚里,大伯是最后一个住进新房的人。
那次看见大伯和父亲一起去逛会,依旧是大伯他骑着车驮着父亲。他们都冲着我笑,形如皱菊一样的瘦脸,豁着牙的嘴,让我忽然想流泪。年纪古稀的大伯越老越看重亲情。时常看见一身布衣的大伯,背着手,从三叔家出来,又到四叔家看看,去五叔家聊聊,再到我们家来,和父亲一起抽烟、喝茶、问询儿女们的境况,诉说各自家里的烦难,互相劝解着,感叹着,有时只是默默地相守着坐一会。兴致好时,大伯也会找他的棋友杀几盘。每次看见年迈的大伯为村里缺劳力的人家打零工,我们总会劝他别再干了,可他总是说,闲着闷得慌,干这些杂活也累不着,挣几个零花钱手头活便,两个孙儿上学,你哥负担不轻的。原指望境况好起来,辛苦操劳一生的大伯也该歇下来,享享清福,可是造化弄人,让人总是措手不及。
望着灵桌前大伯慈祥的遗容,只能默默垂泪。可叹灵前的秦腔折子戏,慢板苦音中,演员凄容哀婉地诉说着人世的悲欢,似乎在追忆,又似在安抚亡魂。灵前灯下那只起舞的飞蛾,也许是大伯幻化的魂魄,久久地不肯同他的亲人作别。安息吧大伯,您会永远活在亲人们的记忆中。